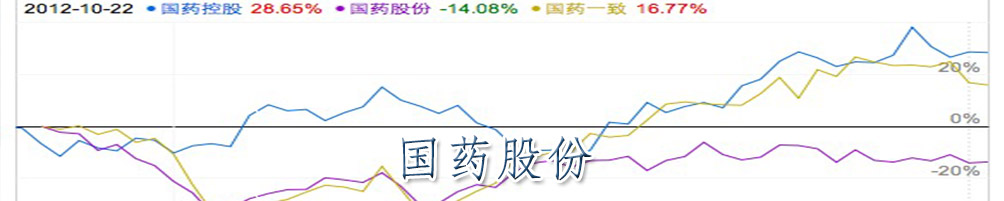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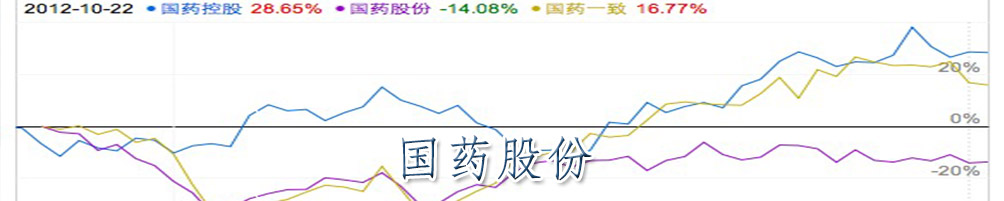
第八章和谐的家庭
1、幸福的婚姻
一九五七年,农历七月十六日我结婚了。妻叫刘玉勤,娘家住在我们东边约八华里处的刘和庄。我的亲事是在我七岁那年父母订的“娃娃亲”。
当时,父亲和母亲的“选媳”条件并不高,只是有点特别。父亲提出的条件是:女方贫富无所谓,一定要知根知底,最好沾点老亲。母亲的标准是:身个要高点,会做针线活,最好比儿子大几岁。事情再巧不过了,说媒的人是我的亲姑奶,也就是父亲的姑母,女方和姑奶是同村,同宗,这完全符合父亲提出的条件。妻那年十岁了,比我大三岁。十岁的女孩已经长得像一个大姑娘了,两条长长的辫子,细长的身段。况且织布纺花,做鞋缝衣,什么针线活都会。妻的条件与母亲要求的标准完全对上了号。母亲高兴地说:“女大三,抱金砖。这个媳妇我要定了。”真是天作之合,父母都很高兴。就在定亲的前一天,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波折。有人告诉父母,说妻不识字。母亲有点犹豫。可是父亲却说:“不识字不算毛病,咱俩都不识字,不是也过的很好吗?”母亲想了想,觉得父亲说得也对,若娶个识文断字的媳妇,说不定还不好使唤呢!于是我的婚事就这样订下来了。那时的婚姻都是父母包办,我什么也不知道。在订婚以后二、三年里,也没有见到妻是什么样子。根本不知道“说媳妇”是干什么的。后来,在父母和亲朋的交谈中,偶尔听到妻比我大三岁,比我个子高。还有人说,小两口打架,儿子一定打不过媳妇。大人们说的“笑话”,引起了我的不安。我恍然大悟了:“啊,原来娶媳妇是要打架的。可我打不过她怎么办?不怕,有奶奶呢,奶奶一定给我‘帮锤’”。
在我十六岁那年,见到了妻。她已经十九岁了,身体发育得完全成熟。站在那里,亭亭玉立,宛如出水的芙蓉。两条乌黑的辫子搭在前胸上,仪态端庄秀美。而我呢,本来个头不高,身体发育得又慢,和妻一比较,我感到自惭形秽。无论怎样看,都觉得自己像老鹰抓小鸡时的“小鸡”。越这样想,越感到浑身不自在。虽然当时我已经知道“娶媳妇”不光是为了“打架”。可总觉得自己太弱小了。初次见面,竟连和妻说话的勇气也没有了。同时,我还有另外一种想法:别看个子小,我是个有文化的人。妻虽然个大,可她是个大老粗,我们没有共同语言。在这种自卑和自尊双重思想的驱使下,我带上一本书,悄无声息地走了出去。
到了一九五七年,我已经是十九岁的大小伙子了。说是大,其实个头并不高。繁重的体力劳动,紧张的自学生活,影响了我身体的正常发育。可二十二岁的妻就完全不一样了,体态丰满,娴静端庄,看起来比我成熟,懂事多了。
说是结婚,实际太简单了。因为我们双方的家庭,都极度贫寒,连一点结婚必备的用品也没有。在我那两间茅屋的里间前墙边,砌了一个土坯床,床上一被一褥,别无长物。妻娘家陪送的嫁妆是:一镜一梳,仅此而已。“新房”内无桌无椅,无箱无柜。这样倒也干净利索。结婚那天,不请亲朋,没有婚宴,小鞭一挂,“啪啪”了事。
结婚虽然草率,但婚后的生活是甜蜜的。奶奶年近八旬,已经不能再纺花织布;母亲劳累过度,体弱多病,我们也不忍心让她再干活了。两个妹妹正在上学。家庭的生活重担,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和妻的肩上。妻在两个老人跟前,从未大声说过话。端饭送水伺候得周周到到。“贤孝”二字放在妻的身上,一点也不过分。
原来我以为,我和妻之间是父母包办的婚姻,双方没有一定的感情基础,文化差异又这样大,恐怕没有共同语言。不料婚后,妻那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性格,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从妻的身上看到了越来越多的闪光点。
2、贤妻良母
在妻的身上,集中闪耀着中国农村妇女贤孝善良,勤俭纯朴的美德。
我们婚后第二年,即一九五八年七月,妻生下了第一个儿子——我的长子本奇。可惜这个孩子的命运太苦了。孩子还没过百天,“在三面红旗照耀下”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开始了。因为营养太差,妻的身体还没有恢复过来,就在村干部的催逼下,抱着孩子到西唐河去淘铁沙。为了照看孩子,母亲也跟着去了。
谁也不会料到,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到这个幼小生命的身上。一个民工回住处取东西,不小心碰掉了挂在房梁上的竹筐。筐内装满几十斤重的物品。我那可怜的孩子,正睡在房梁下面的地铺上。那筐东西恰巧砸在孩子的头上。孩子当即被砸得鼻脸乌青,昏死过去。母亲从外边回来,抱起孩子边哭边喊。有人到河上把正在淘铁沙的妻喊回来。妻抱起孩子哭得死去活来。孩子的小生命非常顽强,在奶奶和妈妈的哭喊声中,奇迹般地又活了过来。可仍是呼吸微弱,气息奄奄。
母亲和妻抱着可怜的孩子,徒步跑了八、九里地,到学校去找我。可我是一个刚参加工作的,没有工资的民办教师,我能有什么办法呢?面对孩子的惨状,我们全家人束手无策。好心的王廷壁校长,给了我十几元钱,我们把孩子抱到诊所,请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又开了几天药。因为没有钱,失去了孩子的最佳治疗期。命虽保住了,可是留下了脑震荡的终生后遗症。长大以后,记忆力差,反映迟钝,生活不能自理。直到现在,还得妻照料他的衣食起居。
妻在这沉重的打击面前,毫无怨言,默默地承受着这无法忍受的痛苦。
在那个时期,我们家庭的贫困程度,说来恐怕没人相信。妻在春夏间只有一身衣服,根本没法换洗。只有在晚上孩子睡了以后,脱下来洗洗晾上。到天明不管晾干没晾干就穿在身上。后来学校一个女老师,看到妻穿的实在可怜,就把自己的一件上衣脱给了她。穿的尚且如此,吃的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堪回首。
跟着我过这种穷困潦倒的日子,妻没有一句怨言,从来没有流露出一点的不满。她每天照常外出上工,回家做饭,伺候老的,照料小的。有一点好吃的东西,她从不沾唇,总是留给老人和孩子。
一九六二年以后,我的三个女儿:淑慧、淑娟、淑凤陆续出生。
这里需要回顾一段历史。
在公共食堂解散以后,农村的管理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公社统一管理,队为基础的核算方式。社员们分成男劳力,女劳力,半劳力等三种类型。每天分别记十分、八分、七分。每十分为一个劳动日。年终统一结算。
在那段时间里,我的两个妹妹都辍学在家,帮助她们嫂嫂干活抓工分,养家糊口。大妹秀荣,天资聪颖,小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方城县第八初级中学(校址在方城县陌陂镇)。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地富子女能考上中学的简直是凤毛麟角。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家庭特别困难,她勉强读完初中,就失去了深造的机会,辍学在家帮助嫂嫂料理家务,养活老小。小妹金荣,也由于家庭原因,仅仅读完小学,就在家参加劳动。
母亲、妻子、两个妹妹,这四个伟大的善良的女性,共同支撑起了这个摇摇欲堕的极度贫寒的家庭。
由于两个妹妹辍学在家,像男孩子一样出去干活,每天挣得的工分比过去多了一倍。尽管当时工分的单值低的可怜(每十分为一个劳动日,每个劳动日最高不到四角钱),但家庭的经济状况总算有了好转。
妻在一九八〇年五月,生下了我们的第五个孩子——小松海。小家伙的出现,给家庭带来了更大的欢乐。
妻的功劳太大了,她一共养育了五个孩子:老大本奇,有残疾不能上学。老二淑慧大学本科毕业,从事教育工作。老三淑娟本科毕业,也在从事教育工作。老四淑凤专科毕业在南阳防爆厂上班。老五松海硕士毕业,现在已参加工作。
妻把善良、聪慧、勤劳、正直的性格传给了孩子们,他们正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共和国的繁荣昌盛,社会的和谐发展忘我地工作着。
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就是对母爱的最好回报!
3、携手相伴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妻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结婚以后,妻替我承担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家务,让我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
一九五八年。
这时农村是“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公社。在农业生产上,实行“大兵团”作战。即在全公社范围内的青壮年男女劳动力,实行统一调动,集中使用,大规模地搞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二十三岁的妻,把生病中的孩子交给母亲看管,自己经常出外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
在“大跃进”中,学校走在运动的前列。我那时日以继夜地工作,开会,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家里的老小。在这段日子里,真是苦坏了贤德的妻子。上文中提到,我那生下来未过百天的孩子被砸伤致残,就发生在这个疯狂的“大跃进”前期。
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二年。
这是国民经济极端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妻常常把自己从食堂领到的一份口粮,再均给老人和孩子一点,自己只喝点稀汤,吃点野菜。我偶尔回家一次,看到妻那骨瘦如柴的可怜样子,就心疼得热泪直流。可是妻却没有流泪,反而替我抹去泪水,安慰我说:“没事,你放心,我饿不死。因为一家老少还得我伺候,阎王爷不要我。”听到妻的话,我破涕为笑,妻太善良了。
一九六六年。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母亲和我在这场运动中,分别挨斗受批,痛不欲生。妻总是千方百计地劝解母亲,抚慰我那受伤的心灵。鼓励我“想开点,夜再长,天再黑,总有天明见到太阳的时候。”谁说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妻和我是两个文化层次截然不同的人。可是我们的心贴得那样近,我们的感情是那样真挚!我们有着说不完,道不尽的共同语言!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国家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崭新局面。
我又重新走上讲台,后来又经过招教考试,转为公办教师。再后来又被聘为小学校长,联中校长。这几年,在我一帆风顺的境遇中,妻还是那个样子:默默无闻地操持家务,照料老小,无怨无悔地支持着我的工作。妻从来没有因为我逆境中遭受挫折而冷落我,抛弃我;也没有因为我的成功,地位的变化而在人前蛮横无理,趾高气扬。妻永远是那个样子:慢声细语,见人先笑。只要有人张嘴、借钱也要帮你。
人往往是这样;在上班时间没有看到的东西,退休以后才会发现。过去我没有注意到老伴有什么变化。退休以后,突然发现老伴的个子好像矮了一截子。经仔细观察,原来老伴那直挺挺的腰板,现在有点弯了。有段时间她一直说腰疼,后来医院去检查,经多种仪器检测后,医生告知,是长期劳累造成的骨骼损伤,脊椎变形。服几天药,就会好点,但是没有根治的办法。最好不要干活,好好休息。可是她闲不住,在家里还是不停地找活干。我感到内疚,是我对不住老伴,让她的体质受到这样大的摧残。
随着老伴的腰越来越弯,我的负疚感也越来越大。
为了弥补我的愧疚,只有从体力劳动上替她多分担些家务。在精神上,多给她些安慰。
首先,我学会了烧火、做饭、炒菜、洗碗。接着,铺床扫地,这些杂活我也争着干。看到我一反常态的这样“勤快”,老伴倒觉得有点不适应。她多次制止我干这些杂活,我没有听她劝阻,越干越顺手,所有家务活几乎全包了。只是没有向老伴说明,这样做我是为了“补过”呀!
除了在体力上给老伴以有力的帮助以外,还在精神上多方给予安慰。我给她讲故事,想法逗她乐,让她笑口常开,每天生活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这样做,可以填补多年来在这方面我对老伴的愧疚。
因为老伴不识字,历史知识等于零。看电视有一定的困难。她爱看戏,可是又不懂戏。不仅朝代分不清,连忠臣、奸臣、好人、坏人,“谁和谁一家”也分不清。于是,我先给她介绍剧情,再介绍剧中人物。随着人物的登场,分别给她介绍忠、奸、好、坏以及剧中人物的关系。这样,老伴高兴了。出去串门,有了对媳妇们“吹”两句的本钱。我就经常这样在看电视剧的时候给她当“翻译”。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老两口也沉浸在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节中。
我和老伴从一九五七年结婚,到现在(二〇一二年),我们已经互相搀扶着,走过了五十五个春秋,足以超过了“金婚”的界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这样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我和老伴将携手相伴,快乐地朝着光辉的未来继续走下去。
敬请期待下期第九章:在“大跃进”的年代里
作者:贺进山是社旗县苗店镇老贺庄村小贺庄自然村人,历任教师、老贺庄联中校长、老贺庄小学校长,现退休。年,写诗歌颂党的领导,受过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南阳日报等媒体的报道。贺老师退休后继续笔耕不断,写出个人纪实自传长篇文学《成长》。
欢迎点击文章标题下方的蓝字“赊旗兴隆镇”或者再下方长按识别白癫风那家三甲好北京什么医院治白癜风比较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