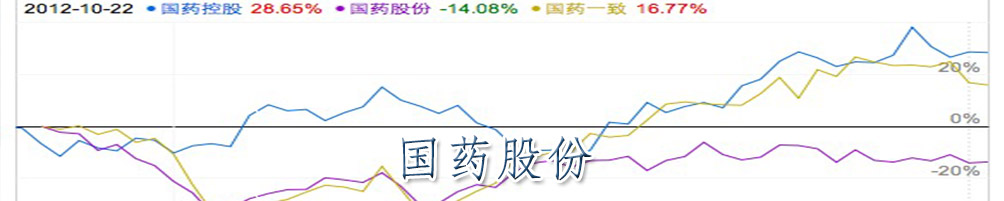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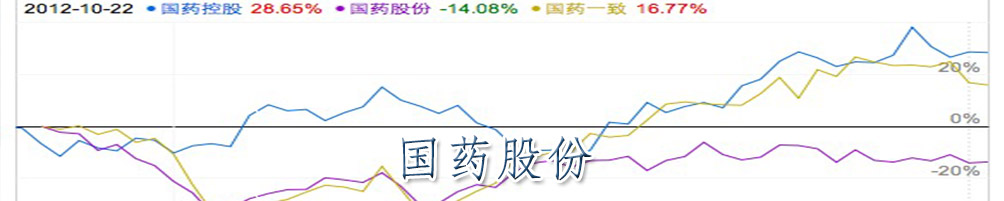
����������֣��Ȫ��70��д���ߡ���С˵����Ϊ�����漰ʫ����ʣ�ż��Ϸ�硣������Ʒ���ڡ�������ѧ�����ջ�ʮ�¡������ϡ������ҡ������ǡ�����ѧ�����Ϸ��������г�ƪС˵�����������������ǡ������нἯ��Ʒ��������⡷�����Сʷ����ij��ij��ij���������������ֵ��١��ȡ�����������ѧ����ƪС˵�����ھŽ졶ʮ�¡���ѧ�����ڶ���������ƪС˵���ȡ�
���������������ȥ�ݿ�
��ح����
�к���ѧ������Զ�볾�����ѹ����Ұ����һ����ɽ�����ڱ���������̸��������˭�����ǿ�ʼ���ź������Ĵ���������λ����ѧ�ӣ���ֻ�ж�ʮ��ͷ������һλ�DZ����ˣ������λ����ʡ�ˡ�������ĵ������ų�����Ϊ�����������͡�����Ҳ���˸��������˸��ºŽС������ꡱ��������ס���������������������ҡ���Ӣ������������������ձ������������������ꡱ�ؾ�ɽ�У�DZ���з�������������һ�ֺ����ij�����������������ż���ӹ�������̽��ͷ�������ſ��ȣ���һ�۴���İ������������Ҳ����һ�ֳ���֮�аɡ�
������ס������Ϻ�һ���������������������Լ���λ�ò����Ϻ����ڴ���ij���յĹ����ң������������θ��ڽ��ڴ��ã��Ƕ�����Զ���ĸ�ɽ����ѡ����ط���Ҳ����һʱ��Ѫ�����ġ�ǰЩ�꣬�����ף�Ҳ���Ƕɿڴ�峤�������ز������֣���һ��Ƭ�μ�غ���������ˣ������Ƭ�����Ĺ�ҵ�������ӱ�ҵ�峤�ʹ�������Ӻ��������쳧���Դ�˩ס���Ľţ����¶�Ʈ�������������ꡱ�Ͼ��ǡ����ꡱ��־����С�����Ը���˵�����Ѿ��ҵ���λ־ͬ���ϵ����ѣ����ĸ�һ������ҵ���峤��Ȼ��֪��������������Щרҵ����Ķ�������������Ҳ�������¿ɳɡ������İ塣������ס�һ���绰���������ҡ��͡���������Ϳ���Խ���ܹ����ˡ�Ȼ������һ�괺�죬����Ҳ���������ˡ�
������ҵ�����Ķɿڴ嵽��Ʈ����������˭��֪���������ǻ��³��ġ���������ȥ��һ���ֳ���ˮ����ȥ��һ���ֳ����˵�ѪҺ��ȥ����ɿڴ�������������ζ�������ȥ�ˡ�
��ô�죿�����豸�������ˣ��ܲ��ܰ�;���ϡ�������ס�������˼ı�������ҵ���һ�����ӣ������ѹ����Ұᵽ�ϼҵ�ɽ��ȥ����ɽ���Ƕɿڴ�峤����ס���ĵط����ڱ��ض���һ�硣�峤����Ǩ��һ����Ȼ�ķ����£���ֻҪ�����ö����⣬Ҳ���ɡ��ϼҵ�����ɷ��ӻ��ڣ�����������ɨ����ˢ�����ã����ǿ���ס�˵ġ�
�ԡ������ꡱ��˵�������Ѿ��ķϵ�ɽ����ɿڴ���ȣ���ֱ����һ����Դ���硣��ɽ����ˮ���в�ľ����һ������Ļ���������ʲô���������㣿������ס�վ����̨�ϣ������̾˵���Ϻ��ķ紵������������ô��Ӳ��������ķ�����͵ġ�
������������ͬ�չ������ˡ���Ȼ����������������ӣ���������Ҫ�Եġ��������ꡱ�Թ������ͣ��ܶ�ʳ�ķǵù��˴�ɽ����������������ס�����һ̨����決�����Լ���������ʽ���⣻�������ҡ�����һ̨��ʽ���Ȼ���������ֻ�ʽ���ȣ����ܴ��ϸ������ĭ����������������ձ��������ﵶ�㿾������ص�������������ƣ���ζ���ѡ�����֮�⣬���ǻ�����һ������ɽȮ��һ������Ҳ�䱸��ר�ŵĹ�ʳ��
�����ɽ���������������������������������ֱȹ���������������������������������Ǹ�ɽ��һ�����Ȱ����Ŀ��������ż����������ӡ�
��ĩ������������ݶ���ƽ̨��֧��һ�Ѱ�ɫ̫��ɡ���������һ�ߺ�����裬һ�߹�����ɽ����ɽ��ԭ��ס�ż�ʮ���˼ң���ʮ����ǰ���������Ǩ���е�ס������ȥ�ˣ��еķ�������塣��Ϊû���˿��ܣ����������һ�յػ�����ȥ�ˡ���Щľʯ�ṹ���Ϸ��ӿյ����ģ��·���ʲô���������澲���ظ��ã�ɢ����һ�ɹŹֵ���Ϣ���Ͱ����ݶ��ϵ����������Ӳݣ�ԶԶ��ȥ��ͬһƬ���£�ż���м�ֻҰ���Ӷ��鰫ǽ�����һ�·��ӵ��ݶ��IJݴԼ䣬����ֻ��֪������
����ʱ�֣�������ס���ɽ������������߶��ˣ����������һ���˼ҵ��ݶ���������һ�ƴ��̡�
�������ҡ�˵�������������į�������������ҵ���ͬ�ࡣ
���������˵������֣���������ߵĶ���Ū����ô�����Ǿ�Ȼ�֪����
������ס�˵��Ҳ������Ϊ������˰����ǿ��������������֣���Ը������Ǵ���
�������ҡ�˵��������ô˵������Ӧ��ȥ�����ݷ���λ������������ھӡ�
������ס�˵���ǵģ����ǻ�Ӧ�������ǹ����Ⱥ������ġ�
���ǣ��ڡ�����ס��Ĵ����£������ƹ�ɽ��һ��С����ѭ�Ŵ�������ķ����߷����ǻ��˼ҡ�Ϊ�˱�ʾ���⣬�������ﻹ������һС����ۺ�ˮ����ͷ���������ҡ��������Ŀ���˵�������������Dz����е���ʥ������������λ���Żƽ����㡢ûҩǰ�������㳯ʥ������ʿ�����������˵������Ҫô�Ǽ�����������ˣ�Ҫô�Ǽ�����һ���������Ŀ��������ɽ������ס�˵����ʮ����ǰ���Ҹ���ȫ����˶���Ǩ��ɽ��ȥס�������������������أ���һ��Ұ��ģ����ϲ���������˹�ٵġ������ҡ���ʼ��������˵��Ҳ��ס�����������һ�����ܵ�ɽͷ���ѵ�ɱ�˷��ء������������Ҳ����ž͵����ǻ��˼ҵĴ��ſڡ�������ס����˼����ţ�û��Ӧ�����ָ��ŵͰ�����ǽ���˼�������һ�����������������Ь����̤̤�ܳ�������֨ѽһ��������¶��һ��С�к��İ����������������Ŀ�⿴�˿�����˵��̫��˵�ˣ����������������ˡ�������ס�˵�����Dz������ˣ��Ҹ�������Ҳ�������ģ��������̫��������ֻ��������һ�£�û�б����˼����û˵�꣬С�к��Ѿ����Źع������������ꡱֻ�ð���������ſڣ������뿪�ˡ�
�ڶ��죬������ס�����ʱ�������ſڶѷ��������ͳ�ȥ�����������ʶ��ɨ��һ�����֣������һ�£���������һ��ϸ�ݵ���Ӱ��бб���������DZ���ȥ��һ���ƹ�����һ��һ�ߵ����ţ���������dz���չ�͵�������Ӱ��ת�ۼ䣬�ƹ����ܵ�ǰͷ��û��ݴԣ�����Ӱ�ѽ����������֣���������ٰ������������Ӱ�ͻ���ʧ���������ġ�������������������������ζ����������˷ܵػӶ����ֱۣ���С�к�Զȥ����Ӱ����һ�����ڡ�С�к�Ҳ��֪��ô���£���ͷ����һ�ۣ�������ǰ�ܣ�û�ܼ������ֻ�ͷ����һ�ۣ�Ȼ��������ƹ�һ��������������ʱ�����ˡ�
Ϊʲô�����Dz�������˵�����������������Զȥ�ı�Ӱ̾Ϣ��һ����
��Ȯ���ţ�������������������ʲô���ã�������ס�˵����������֪��������ɽ�ϻ���һ���ھӡ�
���������˵����������֪�����������ģ�����Ҳ֪�����������ġ�
������ס�����Զɽ˵����ɽ����ס�ţ���ʱ���������Լ��ص��˹Ŵ������������������ȥ�ݷ�һλ�����ѣ���������һ�����õ��¡�
���������˲��ڼң����ִ���һ˿�ź��������������ҡ������ſ�Ц��˵��
С�к���������ɽ����һͷ��������ɽ����һͷ�����Ӿ���ô���š���һ�죬�������ꡱ���ȵط��֣����ǵIJ���ɽȮ�������ƹ��ߵ���һ���ٹ�Щ�գ����Ƿ����Ǹ�С�к�����������һ����Ϫ����Ϸ����Լ���˰�����£������ַ���С�к��������Żƹ�������Ҳ���ɽȮ�档��û�и��������ꡱ˵������������ɽȮ�ƺ������������ֱ����һ�죬������ס��˷ܵ�������С�к����ڸ��ҿ���˵���ˡ����죬������ס��ѹ�ʳ�ָ������ƹ���ͬʱ��Ҳ��һƬţ��ɵݸ�С�к���С�к��ʣ�����ʲô��������ס�˵����ţ��ɡ�С�к�˵���Ҳ������������һ�����С�к�ע���������ϵ�ƤЬ˵�����ǵ�Ь�Ӹ����ǵIJ�һ����������ס�˵�����Ǵ����Dz�Ь�������Ǵ�����ţƤЬ����Ȼ��һ����С�к��ӵɴ����۾��ʣ�ʲô��ţƤЬ��������ס�˵������ţƤ����Ь��С�к����ʣ�ţ���Գԣ�������ס��𣬵�Ȼ���ԡ����ʣ�ţ���ϵ�ƤҲ���Գԣ��ٴ𣬿��ԣ��������Ը��ԵĻ���С�к����˵�ͷ�����Dz������ĵ��ʣ���ȻţƤ���Գԣ���ô�����ǽ��µ�ţƤЬҲ�������˳ԣ�������ס�һ㶣�˵��ţƤ��ţƤ��Ь����Ь�ӣ���һ���ġ�
������ס�˵����С�к���������װ����������Dz�һ�����뷨��
�������ҡ�˵��Ӧ�÷�����˵�������ǵ�������װ�����������һ�����뷨�����ǵ���������ô���ӣ���������ô������СС��ͣ���ɽ����ס�ţ�����֪��������������ô��������������
������ס�˵������ô�������ǰѵ��Դ���ɽ������������Ҳ��һ��ð����
�ǵģ��������ҡ�˵�������DZ���һ������DZ�Ҫ�ġ�
һ����ҹ�����������š������ơ��ܼ����������ꡱͬʱ��һ����ִ��Ͳ��һ����ִ��ǹ������һ��������ȥ���š���һ������ˮ�������������һ�����˵���ײײ�ؽ�����ͷ���ͺ��ӱ��紵��һ�ţ�ֻ�ܿ�������������˰�������ǵ�һ��뷢����һ�£���ͷ���ʣ�����������оȼ���ҩ�������������ˣ���ͷ����¯һ���̣�����ֱ������
�������ꡱ�����ؿ����������������������ҽ��ܣ��ҽа��壬ס��ɽ�ġ���������Ҳ�����ף���ǰ��λ���˾����Ǹ�С�к���˵�ġ�̫�����ˡ�������ס�������һ�²���������ȥ¥���������յ���ҩ�����˽ӹ�ҩ˵��֮ǰ�����Ӻ���һ���в�ҩ������ס��Խ�������ˣ���˵��ҩ��Ч�죬��ָ������ˡ�
�������������������ꡱ�ͳ���ɡ�����ֵ�Ͳ�����˻��͵��ҡ������ɽ����ͨ��ģ������˼���ʵ��ûʲô���õ��ϵ�ļ��õ�����ҹ�������ģ������͵ơ�������ij���ܼ�ª���žɣ�ֻ��һ�������������Ӽ���ũ�ߣ�������һЩ������ʲ���������ң��������һ��Ũ�ҵIJ�ҩ��Ϣ����������ĺڰ����һ�ţ��������ӿ���š�С�к�������һ����ʽ��Բ�������䰡�䰡��������ס�����һ�����Ķ�ͷ����ָ������һ�£������ջء�
����̫��˵���⺢�Ӵ���û�������ӷ������գ�������������ֻ���ó涣ҧ��Ե�ʡ�
����������ʡ�����ס������ó���ʲô�棿������ס�˵������ķ��ԣ�ָ��Щ������ʳ�����ӡ�
����̫��˵�����������õ������¿͡���һ�أ���������ס��������ס����¿͡���ʲô��˼�ˣ����ʣ�ʲô�С����¿͡�������̫��˵����һ�����¼����IJ�����ɽ����ǰ���˷����ⲡ�ģ������������û�м�ʱ���Σ������˵ġ�
������ס����ã�ɽ���˵����Ǵ��ӵģ���Ȼ�Ѳ�Ҳ�����˿��ˡ����������˵�������ǰ����������С�͡������컨��������͡��ġ��������⡰���¿͡�������ͷһ��������Ҳ��ͷһ�ؼ����������ӣ��⺢�Ӽ������ҩ��һʱ���Ҳ�����գ���˾Ͷ���̫��˵����Ȼ���ǿ��ˣ�����Ҫ�ƴ���ȥ��Ҫ�����͡�����ҩ�����Ϳ��õģ�����ġ�
��������ҩ��С�к��ĸ��վ���ˮ�Ƶ�����������ȥ��Ȼ���������賿ʱ�֣����������ˡ������������������ߣ����������ˣ�����������ÿ�ض��ܽ���һ��㡣
�������ꡱ�Թ���ͺ�ͷ�����ͷ�������������������Ƕ�ע�������̫��������һ�����ľ��飬����д�ţ�HolyBible��������ס��ʣ������Ż����̵ģ�����̫���ɴ����۾��ʣ���˵���Ƿ��˽̣������Ҳ��������������ס��ֽ����ʣ���������Լ������õ���ʲô������̫��˵�������ã���ֻ�ǵ�Сʱ�����˲��������Ͱ��Ȿ���������ϣ������ҵIJ����ˣ������Ͱ��Ȿ�����������������ס������ù��������˷�˵������һ��Ӣ�İ�ġ�ʥ������������ö�������̫��ҡҡͷ˵��Ҳ����������������������������Լ��ʱ��������ס�������һ����ң�˵���������Ȼ����Ǯ�ء�����̫��˵������ӥ������ס���ϸ������һ����˵������ī����ң����Ǽ���ô��������Ǯ�ң�����̫��˵�����Ǽ��кܶ�������Ҳ˵�����ˡ��������ꡱ�����⻰��Ҳû������ȥ��
����̫���������һֱû�Ϲ��ۡ�������ס���ο��˵��û�µģ���Ҫ�����ˡ��⡰���¿͡�Ҳ���Ǻ��̺�ġ�����̫��˵���⺢�����ϵIJ������Ѳ��Ŀͣ����Ҳ�ϲ����ء����ҩ�ﲻ�У��Ҿ�ȥ��ɽ�DZߵ�ʦ����һ�ˡ�������ס������������磬�����¶ȼƲ�����һ��С�к������£�ָ��ˮ����˵�����ջ��ڣ�������������һ�ȡ�ʦ����������ˡ�����̫�����ˣ����������ؿڣ�������ʲô�����ո������ˡ����ʡ�����ס������˵���ػ������Ͻ�ʲô���ţ�������ס��������游�����֡����幫���ͷ˵��������ܡ��Դ����˰ᵽʮ�������ɽ�¾�ס֮���Ҿ����Ǽ��������ˡ�����̫������������λ���������Ϻ����𣿡�������������ʼ練�ʣ�Ϊʲô˵�������Ϻ��ˣ�����̫��˵������������ͷ���������Ϻ��ˡ���ʮ����ǰ�����������������һλ�Ϻ��ϰ壬��һ˫ţƤЬ��Ь���Ƕ���һ��С��Ƭ������·���ο۵οۡ��ġ�ȫ�����һ�������������������Ϻ��ϰ����ˡ�
����̫��˵����λ�Ϻ��ϰ��ڶɿڴ���һ������һ����Ƴ����Ѵ��ϵ���Ů���ٶ�����ɽȥ�ˣ�������Ҳ��������̫��һ���߿ڡ�֮�������꣬���ǵ���ȥ�����Ϊʲôһȥ���أ�������֪�����д���˵�����Ķ��ӵò���ʲô�����꣩���ˣ���������Ҳ�������¹ʣ�ʲô�¹ʲ��꣩��ɥ������û����֤ʵ��Щ���Ƿ���ʵ����Ȼ��һ�죬���˰�һ��İ����С�к�����ɽ������������˵�������������̫��˵�������Ǹ������ص����ˣ�������ô���⺢�����������˶�����˵�����ߵ��ˡ��Ӵˣ��⺢�Ӿ�����̫������Ϊ������һ�꣬����̫���������ʮ��
�������˰���̫����һ�������е���������ģ������һ�죬��ͻȻ�������ˣ������⺢�ӹµ�һ����ô�죿������̫������û�������������֡�����̫��˵����λ���������������������˵������ܿ����ʮ������������������ٻ�ʮ���ꡣ���������ʮ����ָ��һ��һ�ٵ�˵���ҽ����Ѿ���ʮ��������
���˴Ӱ���̫���ҳ������ֿ�ʼͬ����һ����������������拉萨最好的白癜风医�?白颠病治�?
ת����ע����http://www.heyixiaosm.com/gsjj/1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