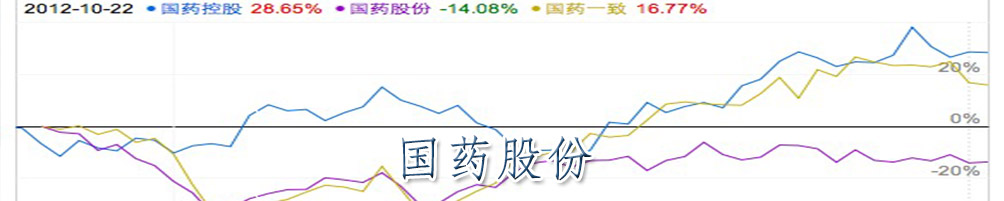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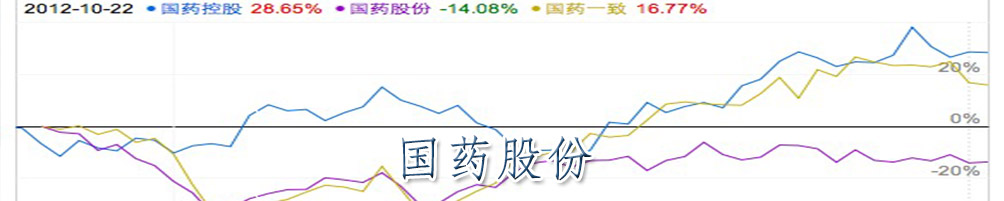
“苏湛,你现在不杀了我,总有一天朕会让你后悔的。”
“苏湛,你好大胆!”
“苏湛,朕不会放过你的!”
伴随着一道惊雷,她从梦中惊醒,满额冷汗。
整整五年了,少年的面容早已经模糊,却偏偏忘不掉那一双桀骜的眼睛。夜凉如水,她咳嗽了几声,抬手去拿床头的茶杯,却被一只冰冷的手给拦截。
“谁?”她一个激灵,本能地去抽枕头下的匕首,恰逢天边划过一道闪电,电光火石间她看清了那隐在黑暗中的脸,当场僵住。
曾经的桀骜少年已长大成人,唯独那双眼睛盛气凌人一如往昔,甚至还夹杂着一股势在必得的狠厉。
她下意识一缩:躲避了五年,到底还是一场枉然。
“苏湛,你逃不掉的。”他的嗓音低哑如幽魂私语,字字惊心,“即便你逃到天涯海角,朕也绝对不会放过你。”
“是吗?那如果我死了呢?”
“你休想!”他骤然抬手扼住她的咽喉,“你是朕的!你的命也是朕的!朕既已经找到了你,就绝不会再让你从朕的眼皮子底下消失!”
她疲惫又苍凉地笑了:“好啊,那你就试试看吧。”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苏湛都是拓跋宸的眼中钉肉中刺。
拓跋宸登基为帝的那一年,年仅九岁。那时江山面临内忧外患,先帝驾崩前急召云南王世子进京,在所有人都以为他是要将世子扣留以防云南王起异心的时候,他却下了一道震惊天下人的诏书——封云南王世子苏湛为摄政王,辅佐新帝登基。
那一年,苏湛十五岁。
更可怕的是,她根本不是苏湛,只不过是云南王最不受宠的一个女儿,她父王舍不得送独子进京做人质,硬逼着她女扮男装顶替进京。
那时候的北魏不但面临虎视眈眈的匈奴,朝中还有强大的外戚势力盘根错节,可这个年轻的摄政王硬是靠着自己的雷霆手段,将这摇摇欲坠的江山给撑了下来。而对新帝拓跋宸来说,她却是一个日益膨胀的威胁。
十三岁的拓跋宸瞪着苏湛的背影,恨得牙痒痒:外戚宦官是豺狼,一个年轻有为的摄政王何尝不是虎豹?若云南王当真起兵造反,和京城掌权的苏湛来个里应外合,江山易主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但他不能将自己的心思表现出来,因为他只是一个窝囊的小皇帝。他资质平平,不通政事,完全无法体会先帝的苦心……就在朝臣们不再对他抱有什么期待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这个小皇帝似乎和从前不一样了。
让他改变的,是一桩绑架案。
拓跋宸是偷偷溜出宫的,为了塑造他不懂事的形象,这些不光彩的事情他没少做。只有他自己知道出宫的真正目的——寻找隐士江群山。
可隐士没找到,他却在一个暗巷中被人蒙头一棍敲晕了过去。他不记得自己到底被关了几天,只觉得脑袋昏昏沉沉不知朝夕,忽然听到门外有打斗的声音,他骤然抬起头,便见一身月白色长衫的苏湛破门而入,单膝跪在他面前,面无表情地为他解开绳索。
他忽然怒意滔天——为什么偏偏来的人是他?!凭什么在他最狼狈可怜的时候,他可以如此光鲜地出现?于是,他狠狠地拍开了她的手。
苏湛一怔,挑眉冷笑:“我救了你,你就这样报答我?”
“谁稀罕你救!”
“好。”她站起来掸了掸衣袖,“我不救,那我走。”
“苏湛!你敢!”
她轻轻地笑了一声:“拓跋宸,如果我是你,就不会这么愚蠢。”
“势单力薄的时候,韬光养晦也许的确是个不错的法子,可也总得有个限度。聪明人应该学会审时度势,该露锋芒的时候藏着掖着,只会耗尽所有人的耐性。你有没有想过,今天这种情况,我随便动点手脚,就可以让你没命回去。”
“苏湛,你敢!”这一声质问明显底气不足,他的掌心爬满冷汗。
“我怎么不敢?之所以没有动手,不过是现在的你还不足以做我的对手。你不是想摆脱我的掌控吗?”她面无表情地盯着他的眼睛,“那就努力让自己变强。示弱也许可以保你一时,却无法让你纵横一世,你只有努力超越我,打败我,才能最终摆脱我。”
他从牙缝中蹦出几个字来:“苏湛,你现在不杀了我,总有一天朕会让你后悔!”
“呵,我等着。”她转身,仿佛从未将他的话当真。
十三岁的拓跋宸盯着她的背影,死死地攥着袖中的拳。
拓跋宸变了。他遣散了伶人戏子,开始奋发图强。朝臣们一边甚是欣慰,一边又开始犹豫该如何选择立场。小皇帝来势汹汹明显是要杠上摄政王,但摄政王的手段又不是没人见识过,若是不小心站错了队……
拓跋宸一直在努力地追着苏湛的脚步,但一次次只能不甘心地发现,与苏湛相比,自己还是太年轻。可明明苏湛当上摄政王的时候也不过十五岁,彼时的铁血手腕到现在都让人津津乐道……他深夜跪在祠堂咬牙切齿:“苏湛再厉害,到底不过是个臣子,朕才是北魏的君王。总有一天,朕会亲政,朕会将苏湛手中的权力一点一点地收回来,只要朕能抓住苏湛的把柄……”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苏湛的弱点竟是那样的。
那是丞相公子的大喜之日,这门婚事是拓跋宸亲赐的,因此他做了主婚人。婚宴上觥筹交错,拓跋宸却心生烦躁,目光下意识地寻找苏湛的身影,却发现她一个人默默地从光线昏暗的地方出去了。他眯了眯眼,匆匆离席,尾随而去。
苏湛独自穿越了深夜的大街小巷,迈进了一家小酒馆。
拓跋宸忽然有些紧张:苏湛为何要放着丞相府的佳酿不喝,偏跑到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小酒馆?这里……是不是有什么秘密?
他失望了。苏湛没有约任何人,只是坐在角落里,一杯接着一杯地喝酒,似乎很痛苦。
他从没有见过那样的苏湛。在他的印象中,苏湛一直都是风光无限的:洞察力敏锐、手腕强硬、自律严苛,甚至有些不近人情。这样的一个人,竟也会这般脆弱?
脆弱?见鬼!他心里嗤笑一声,转身想走,却又止住了脚步。
苏湛醉倒在桌上,老板娘靠近了他:“苏公子?”
拓跋宸一个箭步冲了上去:“你干什么?!”
“我、我只是看苏公子醉了……”
“他醉了我自然会送他回去,不用你操心!”
“哦哦那好,敢问公子您是苏公子的……弟弟?”
拓跋宸勃然大怒:“你哪只眼睛看出来我是他弟弟?仇人!他是我的仇人你懂不懂!”
老板娘受到惊吓:“那、那……”
拓跋宸粗暴地将苏湛拖了起来:“你放心,即便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也不至于现在乘人之危!”
十四岁的拓跋宸身材高大结实,与他相比,反而是二十岁的苏湛瘦弱纤细。他野蛮地将她扔上马车,忽然听到她无意识中的一声呓语。
“沈策。”她只不过是喊了一个名字。
他却如遭雷击——他爱慕的对象居然是今日的……新郎?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难怪这么多年苏湛没纳过一房半妾!这么说他的赐婚棒打了鸳鸯?打得好!
沈策?也不过是一个白面书生而已,有什么好……
拓跋宸的心思千回百转,等他回过神来,恨不得狠狠地扇自己一个耳光!他到底在想什么?苏湛喜欢男人,喜欢什么样的男人,与他何干?!
他猛抽一口凉气,从马车上跳了下来:“你们送摄政王回府,朕自己回去。”
苏湛是真的累了,所有人都以为她强势有手腕,只有她自己知道,她的每一步路都是在铤而走险。她一直在黑夜中踽踽独行,习惯孤单也习惯孤寂,而沈策,就像是黑夜中的一道光,吸引住她的全部视线。
她觉得沈策很干净,明明是丞相之子,却没有半点凌人的傲气,尤其是那双眼睛,有罕见的真诚。苏湛喜欢他,却从未对任何人表露过这份心思。她做得最冲动的事也无非是送了沈丞相一盒沈策爱喝的茶叶,派人去集市上高价买下沈策所有的字画。
她不敢靠近沈策,只是远远地望他一眼便知足,可这点小小的奢求也被拓跋宸给毁了。苏湛觉得心灰意冷,人生无望,可她还是得走下去。小皇帝的羽翼渐渐丰满,他的成长速度让人心惊,总有一天,他会不再需要她这个摄政王。那时候,她总可以解脱的。
只是……最近小皇帝对她的态度有点奇怪。
她去丞相府商议政事,却忽然收到皇上急召,等她赶回皇宫,却被晾在御书房外整整一个时辰;她喜欢附庸风雅,时常会在集市中淘字画,可无论她看中什么都会被神秘人士抢先预定,她派人去查,没想到最后竟查到了皇宫……
她明白小皇帝这是在对她宣战,虽然方式让她哭笑不得。他是君,她是臣,他有任性的权力,她没有。她父王送来的家书言辞越来越露骨,总有一天他的野心会膨胀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她必须抓紧时间布局。小皇帝虽然不够成熟老练,但他聪慧、隐忍、努力,远比她那个窝囊的世子弟弟更适合龙椅。她想守住这个江山,不惜……众叛亲离。
小皇帝的十五岁寿辰将近,她在宫中筹备至深夜,出宫经过御花园,看见拓跋宸一个人在喝闷酒。她本想绕过去,却被眼尖的拓跋宸叫住。
“苏爱卿。”小皇帝似乎是醉了,目光炯炯地盯着她,“这么多年,你身边怎么就没个知心人呢?”
苏湛:“……”
“听说京城里想嫁给你的姑娘可以从城东排到城西?你就没有一个中意的?不如……朕给你赐婚?”
苏湛一怔,诧异地望了他一眼,几次欲言又止,最后也只是垂眸低叹一声:“谢主隆恩。”
“你——”拓跋宸猛地起身,衣袖扫下一大片酒坛子,“苏湛,你好大胆!”
他拂袖而去。
她心底隐隐升起强烈的不安。
疯了!他竟然给苏湛赐婚!而苏湛,居然还敢答应!
拓跋宸狠狠地砸了两个花瓶。自从他窥探了苏湛的秘密之后,竟再也无法直视他。苏湛一定是在他身上下了蛊!还是最迷惑人心的那一种!
他大发雷霆,可是脑子里那个瘦弱的身影却久久挥之不去:苏湛不经常笑,可是一旦笑起来嘴角就会出现淡淡的梨涡,很好看……苏湛最擅长的表情是故作深沉,让人觉得他心机莫测……最难忘的还是那日他醉了酒靠在他身上,身上染了酒香,甚至引他龌龊地想,如果苏湛是个女人……
真是疯了!
不行!他一定要给苏湛赐婚!明天就赐!
可第二天,他还在反复犹豫中,苏湛却已经先跪在了他的面前,语气谦卑:“陛下,微臣今年已二十有一,适婚娶之时,又与顾尚书家的大小姐顾诗诗情投意合,因此想请陛下赐婚。”
拓跋宸惊呆了,有一瞬间他觉得自己的呼吸都要停止,他猛地从龙椅上站起,愤怒的声音响彻大殿:“苏湛,你做梦!”
满朝哗然。尤其顾尚书的脸色瞬间黑了。
拓跋宸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苏爱卿的婚事朕自有主张,只不过朕生辰将至,此事容后再议。退朝!”
回到御书房拓跋宸又狠狠地摔了好几个花瓶,胡乱发泄一通后颓然地跌坐在地上,嘲笑自己:他是帝王,可以拥有后宫三千佳丽,可是他竟然、竟然喜欢上了一个男人!还是他如今亲掌皇权路上最大的敌人——苏湛!
她是实在被逼得无路可退了。
小皇帝为什么突然要给她赐婚?是试探身份?还是想安插探子?无论是哪种可能,苏湛都不能坐以待毙。一旦赐婚成功,她女子的身份迟早暴露。与其被赐一个不知道是谁的新娘,不如她主动去求一桩姻缘。而顾诗诗,是唯一知道她是女儿身的人。
结果还是触怒了他。他的心思越来越难琢磨了,苏湛头痛地揉了揉脑袋。
“苏湛!”顾诗诗大大咧咧地推门而入,“你还好吧?!”
苏湛笑着握了握她的手:“幸好他没答应,不然你岂非要一辈子守活寡?”
“与其嫁给那些臭男人,我宁可嫁给你守活寡!”顾诗诗顿了顿,“我说,皇上他是不是开始怀疑你了?”
苏湛蹙眉,低叹一声:“诗诗,我想放手了。”
“什么?”
“十五岁,已经是可以亲政的年纪,我也该放手了。”
“放手?!”顾诗诗脸色一变,“那你想去哪儿?
苏湛眼中露出几分向往之色:“云游四海,泛舟江上。一蓑烟雨,肆意平生。”
“那……沈策呢?”
苏湛一僵,有种自暴自弃的颓丧:“这份念想……我早就断了。”
顾诗诗拍了拍她的肩膀:“不管你想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的。”
摄政王因病告假一日。
告假三日。五日。十日……
勤勉苛刻的摄政王苏湛竟然已经整整半个月没有来上朝了。朝堂流言四起:摄政王也许并非生病请假,而是被皇上软禁了!你看这几日小皇帝用人用得多顺手啊,三下五除二地就将摄政王的心腹换了个遍。而且啊,好几位大人都曾去探望摄政王,却全吃了闭门羹,只怕这回凶多吉少……
挑衅!这绝对是挑衅!
龙椅上的拓跋宸看着那个空荡荡的位置,越来越烦躁,下了朝就冲身边的宫人吼道:“去叫几个太医,跟朕去摄政王府!朕倒要看看,苏湛那金贵的身子到底生了什么了不得的病!”
他怒气冲冲地往摄政王府赶,眼尖地撞见有人鬼鬼祟祟地从王府偏门出来。他对暗卫使了个眼色,暗卫立即跟了上去。
入了王府,管家拼了命地阻止:“皇上,我家王爷得的是传染性风寒,只怕不妥……”
屋里又传来苏湛的咳嗽声:“微臣身体抱恙,不能给陛下行礼,还望陛下见谅……”
拓跋宸气绝:“好,那就让太医瞧瞧!张太医!”
“微臣在!”
“摄政王可是国之栋梁,你好好给他瞧瞧,可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随即从床帘后伸出一只白皙的手,张太医的手轻轻地搭上了脉搏。拓跋宸死死地盯着那只手,似乎恨不得将它千刀万剐。
“启禀皇上,王爷脉象浮紧,胃寒肾虚,该是纵欲……”
“咳咳咳咳……”床帘内之人迅速打断太医的话,可还是晚了一步,不该听的拓跋宸早已听了去,场面瞬间尴尬无比。
所以,他是因为这等无法启齿的理由才不去上朝,什么传染性风寒根本就是借口?!
“你——”拓跋宸的脸色黑了又绿,绿了又黑,满腔愤懑竟觉得无从发泄,终是化为了一句狂吼,“苏湛,你放肆!”
他拂袖摔门而去。
而床帘内的苏湛却是松了一口气。待所有人都离开后,一个孱弱的单衣公子收回了自己的胳膊,从她身侧惊魂未定地滚下了床跪在地上。
“阿清,辛苦你了。待会儿你去管家那里领二百两银子,离开京城吧。”
“谢、谢王爷。”阿清艰难地从地上爬起,刚靠近房门,房门却从外面被人猛地推开:“苏湛!”措手不及间,他和满脸杀气的拓跋宸打了个照面。
拓跋宸突然震住——苏湛的房间里,竟然还藏着个男人!还是仅仅穿了单衣的男人!难怪……
“苏湛,你不要脸!”拓跋宸怒不可遏,抬脚在阿清身上狠狠地踹了一脚,绝尘而去。
拓跋宸回到自己的寝殿,将整个屋子的瓷器通通摔了个粉碎。
他素来知道苏湛喜欢……可谁知那个人竟然如此荒唐!他气苏湛,更气自己,为什么去而复返?还不是因为不甘心,他好不容易放下身段来探望他一回,怎么能连面都没有见到就回了宫去?可那个人他、他都干了什么?!
疯了!疯了!
更让拓跋宸发疯的,是暗卫带来的消息。
那个从摄政王府溜出去的人,是云南王的探子,身藏兵防布局图。这么多年来,云南王和摄政王一直暗中互有往来,拓跋宸是知道的,也素有戒备。可他没有想到,苏湛他竟真的敢反!
他等着苏湛来解释,整整三天,等来的却是云南王举兵叛乱的消息。
朝堂上乱成一团,可摄政王依旧告假养病。
明明每一个关口的将领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可是云南王的大军却是一路畅通,来势汹汹。短短的五天之内就攻下三座城池,气焰嚣张至极。
拓跋宸不得不对苏湛起了疑心。无论如何,苏湛身为云南王的世子,怎么都无法置身事外。
苏湛被打入天牢,摄政王府被抄,府里搜出了大量与云南王勾结往来的书信,证据确凿。
拓跋宸的心彻底寒透。
夜深人静,拓跋宸独身去了天牢。在最阴暗潮湿的那一间,他看见了躺在草席上的苏湛。他身上穿着最简陋的囚服,可是表情却很淡然,似乎从未后悔,这让拓跋宸几欲发狂:“苏湛,朕不会放过你的!”
苏湛只是苍白地笑笑:“是吗?”
“朕的江山,朕自己来守。至于你,朕绝对不会轻易放过!朕会抽你的筋,扒你的皮,即便朕将来死了,也要你来给朕陪葬!”
“是吗?”苏湛轻嗤一声,“微臣……拭目以待。”
“你——你混账!”
当夜,拓跋宸睡得很不安稳,仿佛梦中一直有一只手死死地扼住他的咽喉。他好不容易挣脱出魔爪从梦中惊醒,忽闻宫人跑来急报:“皇上,不好了!天牢……天牢……”
他掀被而起:“天牢怎么了?!”
“走、走水了!”
惊恐的声音如同一道晴天霹雳,拓跋宸猛地冲出了寝殿,只见西北方向火光一片,照亮了半边天空。
“苏湛!”内心如同城墙轰然坍塌,他拔足狂奔,狂风呼啸而过。
“皇上……皇上!”
“苏湛你出来!朕命你出来!你出来!”他发了疯似的往火场冲,眼看着就要冲进去,被重重侍卫死命地拦下,他目眦欲裂……可依旧无济于事。
熊熊烈火,将他年少时期心中那仅有的一丝悸动,烧了个一干二净。
那一天的黎明,本是他十五岁的生辰。
后来,云南王兵败如山倒,快得就像这场叛乱不过是一场闹剧。
再后来,云南王一家被送到京城问审,苏裕一路破口大骂,什么娘们就是信不得,这么多年他竟养了头白眼狼,苏盈这个畜生。拓跋宸只当他是疯了,挥挥手让人将他带下去,却目光如炬地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倏然从龙椅上站起:“苏湛!”
那人一怔,回过头来,蜡黄的面容让拓跋宸大失所望。
苏裕却疯狂地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小皇帝,即便你如今风光得意又如何,这么多年还不是照样被我那白眼狼女儿耍得团团转?!告诉你吧,这才是本王的儿子苏湛!真正的苏湛!”
拓跋宸刹那间面如死灰。
女人……那个人……竟然是个女人?!
自九死一生逃出来后,苏盈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她机关算尽,谋划出一个天衣无缝的金蝉脱壳之计,顺便还替小皇帝除了心腹大患云南王,最大的代价就是折损了健康。但能换来最珍贵的自由,便是值得的。
她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过了清贫而又安逸的五年。不再需要算尽人心步步为营,她倒是圆润了一圈。可是不知道为何,这明明是她向往的自由生活,心底却漫上一种无限的空虚。
偶尔她会想起沈策,那个干净的书生,只希望他永远不要被官场染黑。
有时她会想起顾诗诗,那如火一般明艳的女子,应该依旧活得张扬明媚。
最后……她会常常想起小皇帝,他气急败坏的样子、他怒不可遏的样子、他隐忍不发的样子……每每想起,她的嘴角总是忍不住轻轻地勾起一抹弧度。但那些都已经模糊,久远得就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事。
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暴雨夜,他会突然出现在她的屋子里,如同鬼魅,如同修罗,扼住她的咽喉,霸道地宣告:“你是朕的!你的命也是朕的!朕既已经找到了你,就绝不会再让你从朕的眼皮子底下消失!”
听上去倒像是情深的话语。可她知道,他是真的恨极了她。她厌倦了,有些自暴自弃地苦笑:“好啊,那你就试试看吧。”
拓跋宸猛地将她从床上抱了起来。她挣扎,却被他死死地摁在怀里。她无奈地妥协:“拓跋宸,虽然我的确骗了你,但也帮了你一个大忙,再加上这么多年为你清扫了不少的障碍,就不能功过相抵吗?即便你当真不愿放过我,如今我也不过是个病残之躯,还能帮你做什么呢?”
拓跋宸的脚步很坚定,他目视前方沉默了许久,才沉沉道:“做朕的皇后。”
她吃了一惊:“皇后?这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你是个女人,而朕是个男人。”
他胳膊上的力道几乎将她的骨头捏碎,她明白他没有在开玩笑:“可我比你……”
“不过六年而已。这五年朕的成长绝对不会让你失望,而你……”他低头意味深长地扫视了她一眼,“几乎停滞不前。”
“你——”她脸颊充血,却忽有所悟,“你是要我帮你打理后宫?”
朝堂上有的是明争暗斗,后宫的斗争更加血雨腥风。他已经弱冠,只怕已经纳了好几位妃子,也许他需要一位有勇有谋有手段的皇后帮他坐镇?
他沉默不语,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有几分跃跃欲试的心思:“好,我可以帮你,但你总得给我个期限……”
“苏湛!”他粗暴地将她扔进马车,“你最好弄清楚,如今的你没有和朕讨价还价的权力!”
她垂眸,淡淡道:“知道了。”
“苏湛!”他又生气了。
“在。”
“做朕的女人,就这么让你委屈?!”
“不委屈,这是微臣几世修来的福分。”
“苏湛,你言不由衷!”
“可这是陛下爱听的。”
“苏湛,你大胆!”
“陛下教训的是。”
“苏湛!”
忽然“扑哧”一声,苏湛忍俊不禁地笑了开来。这么多年,她最怀念的,还是小皇帝那暴跳如雷的表情。平日里他总是假惺惺地叫她“苏爱卿”,只有气急败坏的时候才会连名带姓地吼她。多好,五年过去了,小皇帝还是当初的那个小皇帝……
拓跋宸呆住。他怔怔地望着苏湛脸颊上的浅浅梨涡,浑身的热血都开始叫嚣,他再也顾不了那么多,低头狠狠地吻住了她。
她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他到底有多喜欢她。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他着了魔似的派人在大江南北打探她的消息,一有风吹草动就迫不及待地亲自赶往,已经承受过太多次的期待与绝望。
她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她吸引。那个时候,连他都只能示弱在夹缝中生存,可她却可以那样肆无忌惮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又恨又羡慕,嫉妒得发疯,想毁掉她,却更想将她牢牢掌控在手中。
她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为了留住那个后位,他顶住了多大的压力和舆论。他不需要一个为她掌管后宫的皇后,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有后宫。他要的,只是一个与他并肩共赏这万里河山的妻子。
可那些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找到了她,绝不会让她再次逃离他身边,就够了。
那一天,他终于打探到了她的下落,迫不及待地要寻来,顾诗诗死死拦着他、恳求他:“皇上,即便苏湛一直是您的眼中钉肉中刺,这么多年过去了,您就不能……”
“你错了。”他眯了眯眼睛,指了指自己的心口,回答得极其郑重:“她是朕的心上钉,即便鲜血淋漓,亦割舍不得。”
思及此,他低头将酣睡的她搂紧在自己的怀里,低低地在她耳边轻叹:“唯一的解脱之道,就是将你彻底融入朕的生命里,苏湛。”
叶九意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