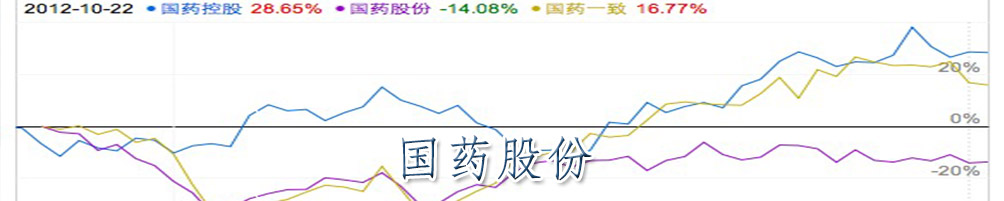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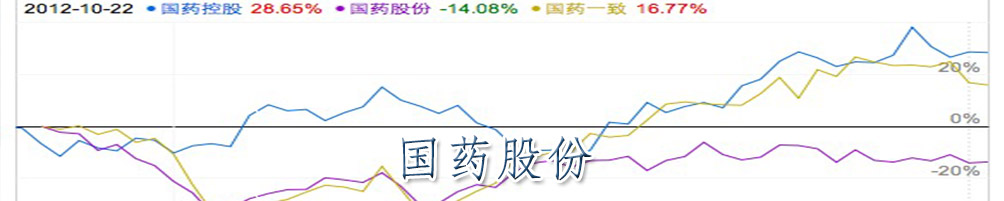
▲年执飞朋友所拍天涯海角
当年的海南无论天多蓝,水多清,对我们而言都不过是个冷然的背景,远不如大安公社饭店偶尔供应的金黄色“炸包”好看——那是油炸的糯米团,包着椰丝、碎花生、白糖,每个一毛。一咬,我的亲妈,满口灿烂!那时天天烈日底下挥锄垦荒,伙食是每月一尝肉,油似有似无,白糖经年不遇,而我所在生产队到公社单程徒步要一个半小时,炸包极难碰到。记得有本理论书说,在英法百年战争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的法国人,绝不会欣赏描绘荒野田园的油画,因为天天在这种场景挣扎,看到就怕。后来社会稳定了、富足了、怀旧了,这种画才大行其道;再后来如您所知,这些油画成了稀世珍品。呵呵,老知青眼里的海南风景,何尝不是这样?▲传说中的黎村,年卡法岭深处
说到乡愁,近年非常流行。细想与古代“去国怀乡,忧馋畏讥”的乡愁不尽相同,带有鲜明时代特色。当代乡愁强烈的,主要是两种人:一是离乡多年,境况有所改善却不易回归故里的人;二是虽没离乡,家乡却已大变,旧貌已难寻的人。一直没离乡、家乡又依旧的人,会有乡愁吗?我想不会。认真地说只有“愁乡”,发愁自己故乡何时能改变贫穷落后闭塞的面貌,发愁自己何时能走出穷乡僻壤,改善处境。发展是硬道理。中国那么多人产生了强烈的乡愁,应该是社会持续高速发展的人文效应,想到“炸包”就止不住咽口水的人,或者已少到可以忽略不计了。不过任何发展都是一把双刃剑,这剑一挥,可能连很多文化情感的老根根,都一股脑儿砍断……话题这就扯远了。▲无数人的例行打卡之地回到天涯海角。那次凭吊,肯定是她亿万斯年孤寂生涯的最后岁月。四五个月以后,扭转当代中国命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北京召开了。随后旅游业的发展,大家都不陌生。后来我陪亲友去过两趟,见到石头依旧,烈日依旧。只是比印象中的椰子树多了十倍,人多了千倍(节假日可能是万倍了吧),门票价格及出门需挤繁杂商业区,都有点不爽……于是再不肯去。我去不去都没关系。天涯巨石据说有了新身份,已经成为年轻人见证爱情“海枯石烂”的圣地,江湖地位不可撼动了。▲这就是她,海枯石烂谁会想到,巨石堆原是这般荒远孤寂。它孑然立于天地间,对人类的一些渺小伎俩,无论是猢狲般在如来佛手指根偷偷撒泡尿、还是理据十足地将它围起来作个自动印钞机,它都毫不在意。它不见证谁,也无需谁的见证。好看还是不好看,到底有多好看,不在巨石,而在心和眼吧。▲景区大门往期文章《琼郡地舆全图》:张之洞治琼理念的艺术宣示史有明载琼南工程遗迹之最——海南唯一宋代人工河二十岁的机场,六百岁的“美兰”他是谁?——一个隔了几百年依然烫手的“热山芋”“出格”府志●罕有治琼能吏——涂公传奇①巨大黑幕●罕有治琼能吏——涂公传奇②条分缕析●罕有治琼能吏——涂公传奇③彪炳功业●罕有治琼能吏——涂公传奇④余波深远●罕有治琼能吏——涂公传奇⑤关于作者知青年代与这座热岛结缘。多年来痴迷海南历史人文,秉承“左图右史”的治学原则,自谓是一名耕古拾遗的民间学者。曾在《岭南文史》《海南日报》《三亚日报》《天涯华文》《现代青年》《中国三峡》等报刊杂志发表学术性文章数十篇,如:《明代琼谚“海热占荒”,最早揭示“厄尔尼诺”》(《三亚日报》.6.12)《明代海南石板驿道的最后遗存》(《岭南文史》,第3期)《最后的黎峒》(《天涯华文》.3)《石门“贪泉”与西华寺探究》(《岭南文史》,第3期)《鉴真在哪里登陆——揭秘湮没已久的崖城古港》(《三亚日报》.8.6)《追寻史图博之“全岛风景最美的地方”》(《天涯华文》.1)《治琼能吏涂棐传奇》(《海南日报》.11.12)《从回辉村乾隆“正堂禁碑”看明清崖州渔课》(《现代青年》第2期)《左图右史读琼州》(共四篇,《海南日报》.5.13)留言区聊两句!
何以拾遗